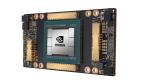深度解析:CUDA Graph 如何重塑大模型“推理性能”邊界
Hello folks,我是 Luga,今天我們來聊一下人工智能應用場景 - 構建大模型推理關鍵技術 - “ CUDA Graph”。
隨著 LLM 的參數規模與應用場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,推理(Inference)階段的性能優化,已從單純追求理論浮點運算(FLOPs)的競賽,轉向一場對系統極致效率的、毫秒必爭的“壓榨”。
在傳統的推理模式中,CPU 作為控制核心,頻繁地向 GPU 下達指令,這種“一問一答”式的交互模式,在面對 LLM 推理任務中海量、細碎的計算核(Kernel)時,其固有的控制開銷(Overhead)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性能墻。
本文將從“架構”的視角,深入剖析 CUDA Graph 這一關鍵技術,闡述如何通過從“命令式”到“聲明式”的范式轉移,將控制權從 CPU 下放至 GPU,從而繞過傳統架構的瓶頸,為構建下一代高性能、低延遲的大模型推理服務,奠定了堅實的架構基石。

一、傳統推理模式的架構之困:CPU 控制開銷的“死亡之谷”
要理解 CUDA Graph 的革命性,我們必須首先審視其所要顛覆的傳統 GPU 執行模型。在一個典型的、未使用 CUDA Graph 的大模型推理流程中,整個系統的運轉高度依賴于中央處理器(CPU)的精細調度。
1. “廚師與幫廚”的命令式架構
我們可以將這種傳統架構,比喻為一個“急性子的主廚(CPU)與一群技藝精湛但需要指令的幫廚(GPU SMs)”的廚房。2者的職責如下:
- 主廚(CPU):負責閱讀菜譜(執行推理代碼),并將每一個烹飪步驟(如矩陣乘法、激活函數、層歸一化等)拆解成獨立的指令。
- 幫廚(GPU):擁有強大的并行處理能力,能夠極快地完成任何單一指令(執行一個 CUDA Kernel)。
整個流程是命令式的:即主廚每喊一個指令,幫廚們就迅速完成,然后集體停下來,等待主廚的下一個指令。對于一個包含數千個獨立操作的復雜菜肴(一次 LLM 推理),主廚需要不間斷地下達數千個指令。問題在于,主廚下達指令本身是需要時間的,這個時間,就是所謂的控制開銷。
2. 控制開銷的“四大元兇”
在 LLM 推理這種對延遲極度敏感的場景下,CPU 的控制開銷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,共同構成了性能的“死亡之谷”:
- 內核啟動延遲(Kernel Launch Latency):CPU 通過 CUDA 驅動程序向 GPU 發起一次 Kernel 啟動請求,本身存在微秒級的固定延遲。對于 LLM 推理中大量的小型 Kernel(例如逐元素的激活函數),這些啟動延遲累加起來,甚至可能超過 Kernel 實際的執行時間。
- CUDA API 調用開銷:除了 Kernel 啟動,每一次內存分配(cudaMalloc)、數據拷貝(cudaMemcpy)、流同步(cudaStreamSynchronize)等 API 調用,都伴隨著 CPU 與 GPU 驅動之間的上下文切換和驗證,累積了顯著的開銷。
- CPU 調度抖動(Jitter):作為通用處理器,CPU 上的推理線程會受到操作系統調度的影響,任何微小的中斷或上下文切換,都會導致向 GPU 發送指令的節奏被打亂,引入不確定的延遲。
- 動態性帶來的重復開銷:對于每一次新的推理請求,CPU 都需要重復地執行幾乎完全相同的邏輯判斷、參數計算和 Kernel 啟動序列,這在架構上是一種巨大的冗余。
在訓練階段,由于數據批次(Batch Size)較大,計算密集度高,這些微秒級的控制開銷尚可被攤銷。但在推理階段,尤其是要求低延遲的在線服務場景(Batch Size 通常為1),這些開銷便凸顯出來,成為限制系統吞吐量和延遲表現的核心架構瓶頸。CPU 成為了那個最慢的環節,導致 GPU 大量的寶貴計算周期被浪費在空閑等待中。
二、從“命令式”到“聲明式”的范式轉移
從本質上而言,CUDA Graph 的出現,并非對傳統模式的“小打小鬧”,而是一次徹底的架構范式轉移:將 GPU 的執行模型,從依賴 CPU 實時指揮的“命令式”,轉變為一次性定義、可重復執行的“聲明式”模型。
基于實際的業務特性,CUDA Graph 的核心思想主要將原本在運行時由 CPU 動態執行的指令序列,預先“錄制”下來,形成一個固定的、可重用的計算圖。這個過程在架構上分為兩個階段:
1. Step 1:捕獲—— 繪制“靜態藍圖”
在此階段,CPU 仍然像過去一樣,按順序執行一次完整的推理計算流。但此時,CUDA 驅動程序會扮演一個“書記員”的角色。它并不會立即將 Kernel 提交給 GPU 執行,而是將 CPU 發出的所有 CUDA 相關操作(Kernel 啟動、內存拷貝、事件同步等),連同它們的參數、依賴關系、執行順序等記錄下來,并在 GPU 驅動內部構建一個有向無環圖(DAG)的數據結構。
這個過程好比主廚不再直接喊菜,而是花時間將一整套復雜的菜譜(例如法國菜“酥皮包鵝肝鴨肉派”)的全部流程,事無巨細地寫成一張標準化的流程圖(SOP),并交給廚房。這就是所謂的 CUDA Graph。
2. Step 2:實例化與執行—— 賦予 GPU “肌肉記憶”
一旦“藍圖”捕獲完成,CPU 的角色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,不再需要重復執行成百上千次的 API 調用。在后續的每一次推理請求中,CPU 只需向 GPU 發出一個極其輕量的指令:“執行這張圖(Launch Graph)”。
GPU 驅動在接收到這個單一指令后,會接管全部的控制權。它擁有完整的計算圖,可以在 GPU 內部,以最高效、最低開銷的方式,調度執行圖中定義的所有操作。省去了與 CPU 的反復通信,繞過了操作系統的調度抖動,實現了 Kernel 的背靠背(Back-to-Back)執行。
這相當于廚房拿到了標準化的 SOP 后,幫廚們便形成了“肌肉記憶”。主廚每次只需喊一聲菜名(“來一份酥皮包鵝肝鴨肉派!”),整個廚房便能心領神會,行云流水般地完成所有工序,中間無需主廚再做任何干預。
通過這種“一次捕獲,多次重放”的架構,CUDA Graph 將原本分散在多次 CPU-GPU 交互中的控制開銷,一次性地攤銷在了初始的捕獲階段,而在至關重要的執行階段,實現了近乎“零”的 CPU 開銷,從而將性能的瓶頸重新交還給 GPU 的計算能力本身。
三、CUDA Graph 在大模型推理中的典型架構應用模式
在復雜多變的 LLM 推理場景中,應用 CUDA Graph 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需要根據具體場景,選擇合適的架構模式。
1. 靜態輸入的完全圖化
這是最理想,也是最簡單的應用模式。當推理請求的輸入形狀(如 Batch Size、Sequence Length)是固定的,整個端到端的推理流程,從數據拷貝到計算再到結果回傳,都可以被完整地捕獲到一個 CUDA Graph 中。
此模式架構優勢主要體現在性能提升最大化,CPU 開銷降至最低。適應于離線批處理、性能基準測試,或業務場景中輸入形狀高度統一的特定任務。
然而,由于其缺乏靈活性。一旦輸入形狀改變,整個圖就需要被廢棄并重新捕獲,這在動態性強的在線服務中是不可接受的。
2. “分段圖化”與“動態參數更新”
在線推理服務的核心挑戰是處理動態的輸入序列長度。一個完全靜態的 CUDA Graph 在此會失效。為此,我們需要采用更靈活的架構策略。這里,我們主要分為如下 3 種架構策略:
(1) 架構策略 1:“分段圖化”
LLM 的推理過程,可以被清晰地劃分為兩個階段:Prefill(對輸入 Prompt 的并行處理)和Decoding(逐 Token 的自回歸生成)。
作為動態性的主要來源,Prefill 階段的計算圖結構與輸入序列長度直接相關。而在 Decoding 階段,由于每次只生成一個 Token,其計算模式是固定且高度重復的。這個階段非常適合被捕獲成一個可重用的 CUDA Graph,我們稱之為“Decoding Graph”或“Step Graph”。
通過將固定的 Decoding 階段圖化,我們已經能夠優化掉推理過程中絕大部分(通常是95%以上)的 CPU 控制開銷。
(2) 架構策略 2:“圖更新”與“動態參數”
CUDA 提供了 Graph Update 機制,允許在不重新捕獲整個圖的情況下,修改圖中某些節點(如 memcpy 或 Kernel)的參數,例如指向輸入/輸出數據的內存地址指針。
這在架構上實現了“結構靜態,數據動態”。我們可以捕獲一個通用的計算圖結構,在每次執行前,通過 Graph Update 將其輸入/輸出指針,動態地指向當前請求的實際數據緩沖區。這避免了為每個請求都重新捕獲的巨大開銷。
(3) 架構策略 3:“裝桶與填充”
這是處理動態序列長度的經典工程實踐。我們可以預先為一系列離散的、有代表性的序列長度(例如 64, 128, 256, 512...)分別捕獲并緩存對應的 CUDA Graph。
在運行時,當接收到一個請求時,我們將其輸入序列填充(Pad)到最接近的、更大的那個桶(Bucket)的長度,然后直接調用該桶預先編譯好的 Graph。
這是一種典型的空間換時間的架構權衡:通過增加內存占用(緩存多個 Graph),換取了在動態輸入下的高性能執行,避免了運行時的編譯和捕獲開銷。
3. 與高性能庫和自定義核的集成
CUDA Graph 并非要取代現有的性能優化手段,恰恰相反,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“調度與粘合”架構。一個設計良好的推理系統中,CUDA Graph 應該作為頂層的調度器,其圖中的節點,調用的正是那些經過極致優化的計算單元。具體:
- 封裝高性能庫: 對 NVIDIA cuBLAS(矩陣運算)、cuDNN(卷積運算)等官方庫的調用。
- 集成自定義核:封裝像 FlashAttention 這樣的 state-of-the-art 的自定義 CUDA Kernel,或是 vLLM 中 PagedAttention 的一系列 Kernel 調用。通過將這些高度優化的、但仍需 CPU 調度的 Kernel 序列捕獲到 Graph 中,實現了優化的“強強聯合”。
綜上所述,大模型推理的性能優化,是一場與物理定律賽跑的系統工程。在這場工程體系中,CUDA Graph 提供了一種跳出傳統思維框架的、釜底抽薪式的架構解決方案:通過將控制權從 CPU 徹底下放到 GPU,實現了從“命令式”到“聲明式”的深刻轉變,從根本上消除了長久以來制約 GPU 推理性能的 CPU 控制開銷。
因此,從某種角度而言,CUDA Graph 不僅僅是一個 API 或一項孤立的技術,而是一種全新的、面向未來的 GPU 編程與調度哲學。
隨著模型結構日趨復雜,業務對延遲的要求愈發嚴苛,CUDA Graph 所代表的“預編譯、圖執行”的架構思想,將不再僅僅是一項“可選”的優化,而是成為構建一切高性能、低延遲 AI 推理服務的、不可或缺的架構基石……
Happy Coding ~
Reference :[1] https://developer.nvidia.com/blog/enabling-dynamic-control-flow-in-cuda-graphs-with-device-graph-launch/
Adiós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