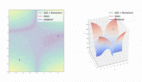一半人明天不上班,GDP不會掉一點!耶魯大學揭AGI殘酷真相
在大多數人的直覺里,只要經濟持續增長,工資總會水漲船高。
可最新的一篇論文卻拋出殘酷預言:在AGI時代,經濟會因為算力擴張而狂飆不止,但普通人的工資卻被「算力成本」鎖死,徹底與增長脫鉤。
也就是說,哪怕GDP翻十倍,你的收入可能一分錢沒漲。
真正的問題不只是失業,而是——當勞動不再驅動增長,我們的價值由誰來定價?

論文鏈接:https://conference.nber.org/conf_papers/f227505.pdf
當工資被算力定價,人類能靠什么漲薪?
在傳統經濟學里,工資往往與「技能稀缺性」掛鉤:你能完成別人做不了的事,就能拿到溢價。
但Restrepo在論文里拋出一個驚悚結論:在AGI經濟中,工資不再取決于你的技能有多稀缺,而是取決于復現你這份技能所需的算力成本。
論文里有一個關鍵公式:
 圖片
圖片
這里的????(??) 表示「用算力復制一個人類完成該任務的成本」。
 圖片
圖片
Restrepo在論文中將經濟活動分為兩類:瓶頸工作(bottleneck work)與附屬工作(accessory work)。
也就是說,一個外科醫生的價值,不再是「獨特技能」, 而是「AGI模擬他所需的算力是多少」。
Restrepo直白地寫道:
在AGI條件下,工資體現的就是復現人類勞動所需的算力成本。
也就是說,不管你是醫生、程序員還是藝術家,在AGI世界里,你的工資上限就是「買幾塊GPU能復現你」。
現實中,這個邏輯已經有了影子。
2025年,英偉達CEO黃仁勛在財報會議上強調,未來的推理型AI模型在算力上的需求可能比當前預期高出100倍,驅動AI經濟的核心將是算力規模,而非更多勞動力。
這和論文的結論不謀而合:在AI公司眼里,人類的勞動已經被等價為算力指標。
更殘酷的是,Restrepo通過模型推導出:當所有「瓶頸工作」被自動化后,產出和算力呈線性關系,而工資則完全與增長脫鉤。
也就是說,哪怕GDP翻十倍,人類的收入依舊原地踏步。
 圖片
圖片
Epoch AI用Cobb-Douglas模型推演了一個結論:當勞動供給不斷增加而其他生產要素不變時,整體產出會繼續擴張,但勞動的邊際產出(也就是工資)會快速下降并趨近于零。
這意味著:未來的勞動市場上,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可能不再是「誰更努力」, 而是「誰更接近算力」。
財富分配大逆轉,算力才是新地主
在沒有AGI的世界里,勞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。GDP上升,工資也隨之上漲。
可在Restrepo的模型里,這條邏輯鏈徹底斷裂:隨著AGI自動化所有瓶頸任務,勞動在GDP中的占比會逐漸收斂到零,幾乎所有新增財富都流向算力資本。
在AGI經濟中,勞動在GDP的份額收斂到零,而算力在GDP的份額收斂到1。
這意味著,算力就像工業革命時期的土地和機器,是決定財富歸屬的核心資產。
誰掌握了數據中心,誰就掌握經濟命脈。
現實里,這個趨勢已經顯現。微軟在2025財年計劃投入約800億美元用于建設AI驅動的數據中心和云基礎設施,創下公司歷史最高資本支出紀錄。
而據《衛報》報道,僅在2025年上半年,幾家科技巨頭在AI上的投入就高達1550億美元,微軟甚至在一個季度內花出超過300億美元,用來擴建AI服務背后的數據中心。
這些數字清楚地說明,資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向算力。
更殘酷的是,Restrepo指出轉型過程本身也會帶來劇烈的不平等。
如果算力供給是瓶頸,那么工資會緩慢下滑,勞動者逐漸被邊緣化;但如果技術突破是瓶頸,情況會更像一場過山車——某些崗位因為暫時沒被替代而迎來工資暴漲,但一旦自動化完成,這些溢價就會瞬間崩塌。
在這樣的格局里,勞動者已不再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,而是被動隨波逐流。
真正掌握財富分配權的,不是靠出賣時間和技能的個體,而是掌控GPU和數據中心的資本巨頭。
AGI讓勞動價值逐漸歸零,卻讓算力成為新的「地主經濟」,重寫了財富的流向。
算力不愿覆蓋的角落,才是人類的歸宿?
AGI并沒有讓人類徹底「無事可做」。
Restrepo提出,除了瓶頸任務被全面自動化之外,還會有一類「附屬工作」(accessory work)可能留給人類。
這類工作并不決定經濟增長,但依然有社會價值,比如照護、陪伴、藝術、娛樂,甚至某些法律、宗教或社區活動。
附屬工作是非必要的,即使保持固定或受限制,也不會阻礙經濟無限擴張。即使某些附屬工作從未被自動化,也只是因為不值得浪費寶貴算力去做。
也就是說,人類并不是被徹底取代,而是被「邊緣化」到那些算力嫌棄不想碰的角落。
 圖片
圖片
IMF經濟學家Anton Korinek提出兩種可能:如果任務復雜度沒有上限(左圖),自動化將無限推進,人類工作空間會被不斷壓縮;如果復雜度有上限(右圖),自動化在某個點會停下,人類可能保留一部分永遠不被替代的工作。
比如,在護理、心理治療、餐飲或藝術表演中,「人類的溫度」可能依然難以被AGI高效復制。
但這類工作提供的不是持續上漲的收入,而是一種被需要的社會意義。
現實中,類似情況已經出現。
大阪大學2023年的一項研究,讓認知能力下降的老人連續數月與陪伴機器人相處。
 圖片
圖片
機器人撤走后,老人們普遍感到孤獨和失落,但依然認為與機器人共處期間的關系是真實而有意義的。
另一項發表于2024年的研究顯示,美國老年人歡迎陪伴機器人輔助娛樂、提醒吃藥,但同時對其「情感表達的真實性」、成本和隱私問題持懷疑態度,
這些案例印證了Restrepo的推演:附屬工作在經濟上是「無關增長」的,卻在社會層面保留著不可替代的角色。
然而,Restrepo也提醒我們,這并非好消息。
因為附屬工作的工資上限依舊由「算力復現成本」決定,而算力擴張不會推高這些工作的價值。
這些崗位可能為人類提供穩定和延續,但不會成為財富增長的來源。
這意味著,未來社會可能出現一種撕裂:經濟高速奔跑,人類卻被留在原地,只能靠「情感勞動」證明自身的存在感。
AGI讓人類「不會被想念」,但或許依舊會被需要——只是那種需要,已經與財富和增長無關。
當財富用算力衡量,紅利該如何分配?
如果勞動在GDP中的份額注定歸零,那么AGI時代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:新增的財富要如何分配?
Restrepo在論文結尾點出了一個關鍵矛盾:生產力增長不再依賴人類勞動,而是依賴算力資源,那么收入自然會流向算力所有者。
所以,我們必須考慮新的分配機制。
在一個由AGI驅動的經濟中,財富最終流向算力的控制者。解決方案之一是將算力收益普遍化為全民分紅,另一種可能是將算力視為類似土地或自然資源的公共資本。
未來的關鍵,不在于我們如何「保住工作」,而在于社會能否建立制度,把算力帶來的紅利重新分配。
在現實中,這種想法并非空中樓閣。
挪威的石油基金已經提供了一個示例。通過對石油收益的全民分紅,挪威把稀缺資源轉化為公共福利。
問題是,這樣的制度能否落實?算力的集中化趨勢讓人擔心。
微軟、亞馬遜、谷歌正在大規模壟斷數據中心和GPU供應鏈。
當財富越來越集中,算力如果完全私有化,社會撕裂只會加劇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「算力紅利」可能不是可選項,而是必要選項。
否則,AGI帶來的繁榮將只是一小部分資本的盛宴,而絕大多數人只能在邊緣工作里掙扎求生。
Restrepo的推演,擊碎了我們對「努力就能換來增長紅利」的直覺。
AGI把瓶頸工作交給算力,把財富集中到數據中心,讓勞動逐漸退出歷史舞臺。
人類并非完全被淘汰,而是被擠到那些無關經濟增長的「附屬崗位」,繼續提供情感、陪伴與意義。
真正的問題已不再是「會不會失業」,而是「我們在一個不再需要我們的經濟里,如何被記住」。
經濟會繼續狂飆,人類卻可能留在原地。
AGI時代,最大的危機不是貧窮,而是無關緊要。